难忘那段时间
发布时间: 信息来源: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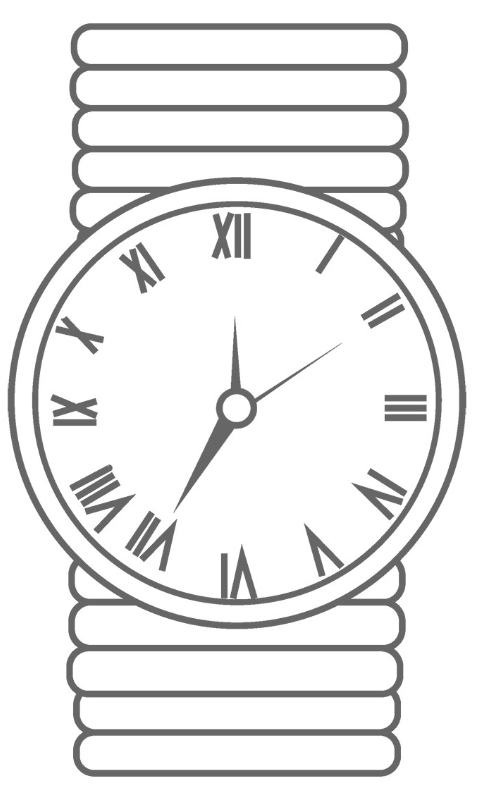
□赵长春(新乡市)
手表,看时间的工具。现在,除了有些人作为身份的表达外,看时间的作用基本没了。
可是,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乡下,谁家有块手表,是很富足的象征。对于我来说,特别盼望家里有一块手表,这样,就不会有以下悲喜交加的上学故事了。
那时候,很怕阴雨天,公鸡打鸣也不准了。估摸着时间到了,父母喊我起床,急忙往学校赶。或者早,或者晚。早了,就在校大门口等。晚了,教室门口罚站。为这,没少成为第一个到校的,也没少在教室门口站着,跟着同学们一起早读。
还怕深秋的晴天,那时候的月亮格外亮堂。隔着纸糊的窗户,屋里一片白。我急忙穿衣,怕惊动父母,背起书包就往学校跑。有句歌词“月亮走我也走”,应该改成“我跑月亮也跑”,月亮好像怕我孤独似的,就在头顶的树杈上跳跃,陪着我跑。路上没有人,更加坚定了我“迟到”的判断......可是,学校大门依旧铁锁。就再跑回来,蹲在灶屋的柴草里,再睡一会儿觉后,家里的公鸡才打头遍鸣!
小学二年级,是在一个叫竹园的村里读的。村子后面一片竹园,很美,被一条小河隔着。上学去,走小路比较近,但是得沿着河岸、田埂,路边还有几个坟头。怕的是下大雨,水声哗哗,竹园呜呜。傍晚回家,河沟漫水,就顶着书包,手拉着手,一步步挪。不敢看水,一看头晕。水打着漩涡,摇着腿,推着你往下游,吓人!好在大人们来接了,晃着手电筒,我们才松了一口气,有的女生就哭出了声,一脸苦楚。后来,微信群里谈起这些,大家觉得成为笑谈。可是说着说着,表情成了泪脸。
下大雪的早晨,我到学校早了,实在不想折腾了,就翻墙进到学校,将教室的门挪开了一道缝,挤进去。教室后面,放着防寒的柴草,是每一名同学从家里带来的,以便天冷时课间烤火。我偎着柴草,手脚冰凉,浑身哆嗦,就取出一把柴草,到教室前面点燃,拢起一堆火......同学们一个一个来了,大家都围着火取暖。老师来了,也不批评我们,再拿来一把柴草,“唉,咱们乡下人真是太受罪了。城里的学校,有煤炉,有暖气......”我有时想起来就会抱怨自己没有在城里出生。
我盼望有块手表,想知道准确时间。可是,那时候整个村里,就中心小学校长有块手表,听说是专门配备的。因此,校长还兼着敲钟的活儿,告知师生上下课。而分散在各村的班级,教室前面埋块石头橛子,老师看日影的长短,估摸着放学的时间。
就这样,我们在模糊的时间中,努力地上学、读书......那时候,每一位老师都告诉我们,好好学习,考上好中学,考上好大学,到城里去工作、生活,“咱们乡下太苦了!”
这种环境下,我特别珍惜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,珍惜父母咬牙供给我读书上进的付出。
一步步,我考上了乡中、县里的高中,依然保持着早到学校的习惯。有个秋天的周末,在家帮着父母收完红薯后,回学校时间来不及了。我就在第二天一早,往学校赶。踏着田野的晨霜,听着一村又一庄的鸡啼,我来到学校大门口时,天才朦朦胧胧发亮。卖早餐的老板刚做好胡辣汤,看我背着书包、提着一网兜馒头,站在风地里,邀我进店,给我盛了一碗汤,满满的、热腾腾的,“吃吧,一会儿包子就熟了......”老板招呼着说。
我没有吃包子。就着汤,泡暄了带的馒头,吃喝起来。
这是我印象深刻的一碗胡辣汤,老板不要钱,还让我在店里暖和,等到学校大门打开。




